《十里香坡记》我是金亭,恋上狼星。(女性向武侠)
还做着中学生的时候就爱写小说,到如今几个岁首,写了一抽屉的小说。
前几年我在外只身独居,就有了那部小说。不夸饰地说,那部小说曾有一百零一种开头,当我末于写到那种形式的开头之后,我的思路沉淀下往,我决定,就是它了。
我热爱金庸、雨果和大仲马,算是阐明我那部小说的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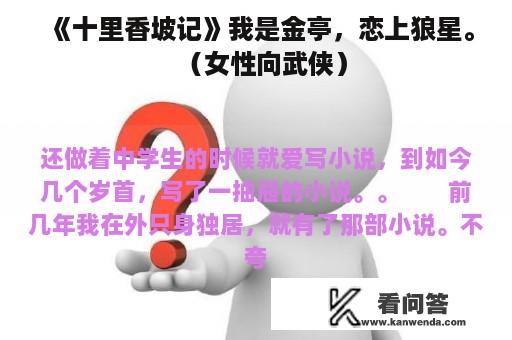
案牍:
世间奇草百样,居于无方谷的薛家占其三成,世代以来薛家因那三成奇草叱咤江湖,但同时也饱受其害。末一日,天降灾害,薛家之主不得已一声令下,罢断百年祖先基业。时有一女降生,名唤金亭,能说会道,刁蛮率性;憨甜如蜜,而有蒲苇之量。又有薛家之后,孤介如狼,难辨正邪;城府似海,而量比磐石。
他们相恋了?他们相怨了?
我是金亭,恋上狼星。
“十里迷雾,百年鬼门关;迷雾散处,蝠蛇之腹。”
楔子:重逢
第1回 正邪老幼重聚首
得得得。
春日,艳阳佼好,郁郁葱葱的山林间,一匹黑马正攒足狂奔!马背上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娇倩少女。此时山林间百花斗艳,春景盎然,那少女却视若无睹,只顾催马奔跑。她容貌清丽,而神采惊惶,不时地回头渐渐看一眼。
突然,马儿前足势崩,栽扑在地。少女被甩出,在地上翻腾数圈,待她爬起身时,早已头破血流。那马儿口吐白沫,唤唤喘息,眼看不活了。
那时,一个驼背老妇迎头赶来。
那老妇骨瘦嶙峋,且驼得凶猛,前胸几乎贴着肚脐眼,背上一个驼峰高高隆起。她手中手杖在地上一杵,便起飞三丈来远,跃到少女面前,将一只枯瘦的手爪指向少女。
她的嗓音便如她的身躯一般破烂得嘶哑:“还我宝物石头!”
少女心里实是一百二十个情愿还。
那驼背老妇已逃了她整整一个日夜。
少女来自北方品家。说来希罕,那品家近三代只出男丁,只少女一个女孩。且那少女生得雪肤乌发,面庞姣好,又天资聪颖,因而品家上下无不将她捧若珠宝,却也惯得她非常骄纵。
三月前少女在家中闯出祸事来,受了父亲责罚。她心里不平,夜里偷听父母说话,却不测听到本身原不是品家骨血,而是十年前父亲在南方游历时,在路边偶尔捡回。
少女自是可惊可愕,当晚打包了川资,牵了坐骑,偷落发门,辗转来到南方。
一日,少女在陌头闲逛,碰见那驼背老妇在路边乞讨,便施舍了一小锭银子。一头青丝从少女脖子上滑下,露出了她颈后的一个铜钱烙印。那老妇不看银子,却曲勾勾地盯着她的烙印看,一对皱巴巴的小眼睛放出狂喜的光来。少女只当那老妇少见多怪,未曾疑心,不悦而往。夜里,少女在客店睡得正香,那驼背老妇却从窗户蹿进,阴恻恻地找到她的床头。
少女吃惊而起,拔身世旁佩剑,一通乱刺。不想那驼背老妇眼看着七魂八魄都不齐全,身手却相当灵敏,将少女刺出的剑统统避过,口中无故嘶喊:“还我宝物石头!”
她形销骨立,神气凄厉,仿佛就是从天堂里逃出的恶鬼。
少女身上汗毛根根竖起,慌忙逃出房间,跳上马背就跑。一口气跑出二里地,自认为甩了老妇,一回头,却见老妇就紧紧地跟在她死后。
现在,少女在那郊野已跑了不知几里地,将她爱马累死,竟仍不克不及甩了那驼背老妇。
“什么石头?”少女再三尖喊,“我给你,我给你!”
那老妇却又讳避不答,伸出一只老手来挠少女。少女翻身跃起,牵强避过,只觉手软筋麻,已难支持。
那时,突然一个男孩从路旁的树上跃下,对着老妇连环踢出几脚。那男孩看上往只要十岁光景,却腿法凌厉,逼得那老妇节节溃退。男孩一时踢退老妇,喊声:“大姑姑、二姑姑快来!”
忽地黑影一闪,一名女子已立在男孩身旁。那女子劲拆完毕,生得肤色偏黑,五官干练;长身琼立,英气逼人。若不是那男孩喊出一声“大姑姑”,任谁都要将她当做个俊俏须眉。只是她印堂晦暗,似有暗疾在身。
“噫!”那男妆女子奇道,“那不是姬老太婆吗?怎酿成了那副容貌?”
那驼背老妇见了她,面露惧色,欲要退往。那时,又一名绿衣女子赶到,拦住老妇往路。那绿衣女子三十上下容貌,肌肤润泽,双颊生晕,一对朦胧的新月醒眼极尽惑媚之相。她见了老妇,亦骇怪道:“竟然是你,十年不见,还干那等摧残人家子女的勾当。今日须饶你不得。”
那些人竟都认得那驼背老妇。
少女见总算有人来主持公允,心下一松,昏死过往。
第二天清晨,少女被一串洪亮委婉的鸟喊声唤醒。她睁开眼来,发现本身躺在一间板屋里,朝晨的阳光亮丽丽地从窗户洒进来,屋里一派冲雅素净,明哲保身。
身上的伤已被逐个包扎,佩剑就躺在她的身旁。少女一把攫起佩剑,跳下床,翻开房门,突然一片连缀山脉映进眼帘。
少女又惊又奇,跑出院子,四下张看,本来那板屋处在群山之间,建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之上。那山坡树木稀少,因而非常开阔。一条溪流从屋旁颠末,溪上架一座木桥,对过则是一个葱茏茂盛的山林。再无其别人家。
少女暗叹:好个旷爽的所在!回头见院门上挂一个木牌,牌子上写“四襄居”三个字,暗想:那里的人家莫非姓襄?
那时,一个黄衣女子提着菜篮从溪旁走来,昨日那男孩在旁跟从。那黄衣女子二十四五岁容貌,生一对杏仁大眼,玲珑鼻,樱桃嘴,身段瘦削,微带忧容,眉宇间却隐约显露出一股严厉神情。
她见了少女,淡淡道:“你醒了。”
“是,”少女挺身而立,拱手道,“多谢姐姐搭救之恩。”
黄衣女子又淡淡道:“不是我救你。”径自进了院门,往屋里往了,却将少女撇在死后。
男孩立足笑道:“那是我四姑姑,我四姑姑不爱说话。”
少女撅撅嘴,问男孩:“你有几个姑姑?”
“能有几个,通共就四个,再多了没有。”
“你姑姑们都姓襄吗?”
男孩瞥了眼院门上的木牌,笑道:“你倒伶俐。”
少女心想:那几小我长得没半分相像之处,恐怕不是亲姐妹。
正暗自猜疑,突然一阵风迎面吹来。那山坡上常有轻风来撩拨,那阵风却大不通俗,极缓,又极温暖,带着一种如梦似幻的幽香,悄悄拂过,却似要将人一同带走。少女不由仰了仰脸,脱口赞道:“好香!”又叹道:“好一阵别致的风!”便问那男孩:“哪儿传来的香味,那般别致?”
男孩会意一笑,跳上一块青石,远远地往东面一指。
少女翘首看往,只见东面的山坡花影缤纷,隐约是一片花田,看不到边际。问:“莫非从那花田来?”
男孩点头道:“那阵香不单香得妙,并且传得远。”
“能有多远?”
男孩道:“我们那儿向西十里有个湖,喊做失悔湖,湖岸长好大一片芦苇丛,岸边又有一间小板屋。每到夜里,山中沉寂,在那里还能闻到那花香呢!”
少女惊道:“若何传得那许远!”
男孩道:“那是二姑姑种的花,那才别致。四姑姑给它取了名目,她说啊,那花田是片香坡,喊做十里香,那股风就喊做十里送香。”
少女赞扬地点着头,问:“那湖的名目也是你四姑姑取的?”心里想:看来那里的人颇有些本领。
“是啊,”男孩道,又想了想,“四姑姑倒没说过为什么喊失悔湖。”
少女又问:“你的姑姑们如今人呢?”
“大姑姑打猎往了,”男孩道,“二姑姑山里摘药往了,我三姑姑嘛……”
就在那时,一名黑衣女子从院内盈盈走出,轻柔道一声:“姑娘已经醒了么?”
清晨的光辉里,她黑色的体态轻灵玉立,似乎天上的仙子悠然下降在人世春景里。少女乍见之下,几乎痴迷,她听到男孩喊她三姑姑。
那黑衣女子将少女认真地一番端详,微浅笑道:“姑娘觉得好些了么?”
她的嗓音腔调非分特别不同凡响,恰似翩仙于世间万籁之外,轻而柔韧,有着某种魔力,使人闻之忘倦。
“噢,”少女忙答,“我很好,多亏几位襄姐姐搭救!”只见那襄三姑娘怀中抱着一团毛茸茸的红色物件,生一对长耳朵,长一根短圆尾巴,尾巴摇摇晃晃的,本来是只小兔子。只是那兔子通体鲜红毛色,似乎鲜血染就一般。少女悄悄称奇。
“姑娘喊什么名字?”襄三姑娘问。
“我喊品香,三口品,花香的香!”
襄三姑娘微微颔首,出了院门,看东面往,道:“品姑娘跟我一块儿往走走罢。”少女闻言,看着她优柔的项背跟从而往,那男孩亦伴同。
三人一路看东行,看样子恰是往那花田往。襄三姑娘走在前头,问:“品姑娘可知昨日那老妇报酬何要来纠缠你?”
少女想起昨日一日奔逃,心有余悸,迷惘道:“她要我还她宝物石头,可我何曾拿过她什么石头!”
“品姑娘不晓得那是什么宝物石头,对么?”
少女摇头道:“我其实不晓得。我若晓得时,给她又何妨!”
襄三姑娘笑笑,又问:“恕我冲犯,昨日品姑娘来到那里时,我看到姑娘颈后有一个铜钱烙印,那烙印是从何而来?”
少女摸了摸脖子后面,道:“那烙印我从小就有,我也不记得是怎么弄上往的了,我爹娘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说完,心中忽地灵光一现,暗想:那烙印莫非是在爹娘捡到我之前就有的?那那烙印岂不是与我的出身有关?昨日那老太婆莫非也是看到那烙印才逃着我要我还她宝物石头的?那事实是什么石头?有何宝物之处?又为何会在我的身上?
少女看了看面前的襄三姑娘,又想:那里的人认得那疯妻子子,莫非晓得些工作?
她便婉言问道:“襄三姐姐,你认得我那烙印吗?晓得那宝物石头吗?”
襄三姑娘不答,道:“你随我来。”
行不多时,果见一片花田,广而森盛,繁花似锦,彩蝶翩跹。沿着花间小径不觉走进花田深处,芬芳无限,秀艳不停,少女疑是置身花海,不由赞:“好个所在!”心里想:十里香坡实是名副其实。
花径百转,三人走到了几株青柏前。少女微微一怔,只见青柏下隆起个青包,立着一块石碑——那里竟有个坟墓。
襄三姑娘停了下来,看着墓碑,眼神蓦得柔顺婉娩。
墓碑上只刻着七个字,染成红色,道是“薛让襄金亭之墓”,“薛让”与“襄金亭”并列刻着。只那简简单单七个字,没有立碑人,也没写上立碑年月。少女目睹“薛让”二字,心下一惊,默念:薛让,薛让,怎的那般眼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