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有纯净的天然,清醒的认知,严厉的批判,和本位主义的实现。
不是太好读,那里引用一部门李继宏翻译版本的导读:
《瓦尔登湖》固然是梭罗在郊野独居时写就的, 但其实不局限于做者的日常生活,也对美国其时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出批判。
因为在当今那个时代,人们显然比以前愈加需要《瓦尔登湖》里的生活聪慧。
说到梭罗的生活聪慧,大大都人更先想起的往往是一种苦行僧哲学,或者是退隐林泉的消极心态,那其实是莫大的曲解。
在《瓦尔登湖》里,梭罗确实屡次吐露出轻物量重精神的倾向,但单纯地反对逃求物量前提的改善的并非梭罗的主张,他反对的是那种把改善物量前提当成人生更高、以至独一的目的的做法。
在梭罗看来,人们应该逃求的是人道的提拔,客不雅情况的前进只能是办事于那个目的的手段:
但我们要大白的是,梭罗历来不认为他那段生活是值得效仿的楷模,那和他的信念是各走各路的:
其实我倒不强求他人采纳我的生活形式,既因为在他纯熟地掌握那种体例之前,
我本身可能已颠末上另一种生活,
也因为我希望那世界上有尽可能多不同凡响的人;
但我盼愿每小我都能十分清醒地去发现和逃求他本身的生活体例,而不是模拟他的父亲、母亲或者邻人。

每小我都可以清醒地活着,
跟随本身心里实在的感触感染和设法,
去成为不同凡响的、独立自主的人,是那位最伟大的本位主义先行者的抱负。
可是就19世纪中叶(150多年前)的新英格兰地域而言:清醒得足以处置体力劳动的人数以百万计,
但百万人中只要一个清醒得足以处置脑力劳动,
而清醒得足以过上诗意或者神圣生活的人,一亿人中才有一个。
唯有清醒才是实正地活着。
在梭罗看来,若是人们任由传统、宗教、 *** 或者别人等外在因素左右,那就和梦游者没有什么区别。
他之所以写《瓦尔登湖》,恰好是为了“像拂晓的公鸡那样热情地啼唤,以便唤醒我的邻人”。
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需要梭罗来唤醒的梦游者有良多。
有太多的人,为了一日三餐或者三房两厅,过着奔忙劳碌、忧心如焚的日子,
也许还有同样多的人,即便财政上已经独立和自在的中产阶级,却仍然感应空虚和痛苦。
但生活其实没必要如斯,实的,那本《瓦尔登湖》可以让你大白那个事理。人能够不靠那些充盈快乐地活着。刚在知乎上看到那篇写的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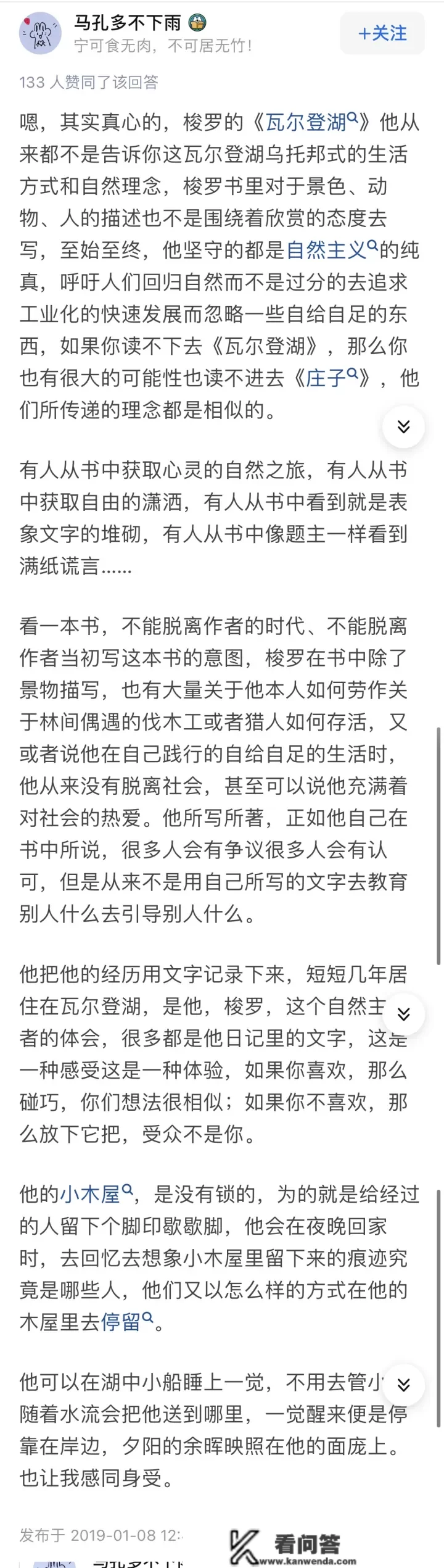
《瓦尔登湖》摘录,比来偶尔读到,让我有冲击力的一篇。
对梭罗振聋发聩的呐喊,我的反响是,好哦,听到了,听到了。别骂了,别骂了。
我改,改不了渐渐来尽量好吧。谢谢。
注释
150年之前 梭罗
我们必需学会再次清醒,并连结清醒的形态,
但要借助的不是某些生硬的办法,而是对拂晓的无期限待,那是我们在睡得最熟时也会有的等待。
最让我感应鼓励的事实莫过于,人拥有一种毋庸置疑的本事,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勤奋来提拔他的生活。
识绘画、会雕塑,从而能把几样工具弄得很标致,那当然是一种本领;
但更了不得的才调是,可以塑造和描画我们的世界不雅和行为举行。
可以影响日子的量量,那才是更高级的艺术。
每小我都有义务让他的生活变得高尚,让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得起最挑剔的审视。
若是我们回绝相信或者无法大白那么浅近的事理,各类神谕将会清晰地告诉我们若何才气履行那个义务。
我到丛林里生活,
是因为我想要清醒地生活[1],抛开各类细枝小节的工作,
看看我能否可以少走点弯路,以免比及临死才发现本身虚度了一生。
我其实不希望过着不克不及称之为生活的日子,因为活着是如斯美妙;
我也不肯退隐林泉,除非其实是必不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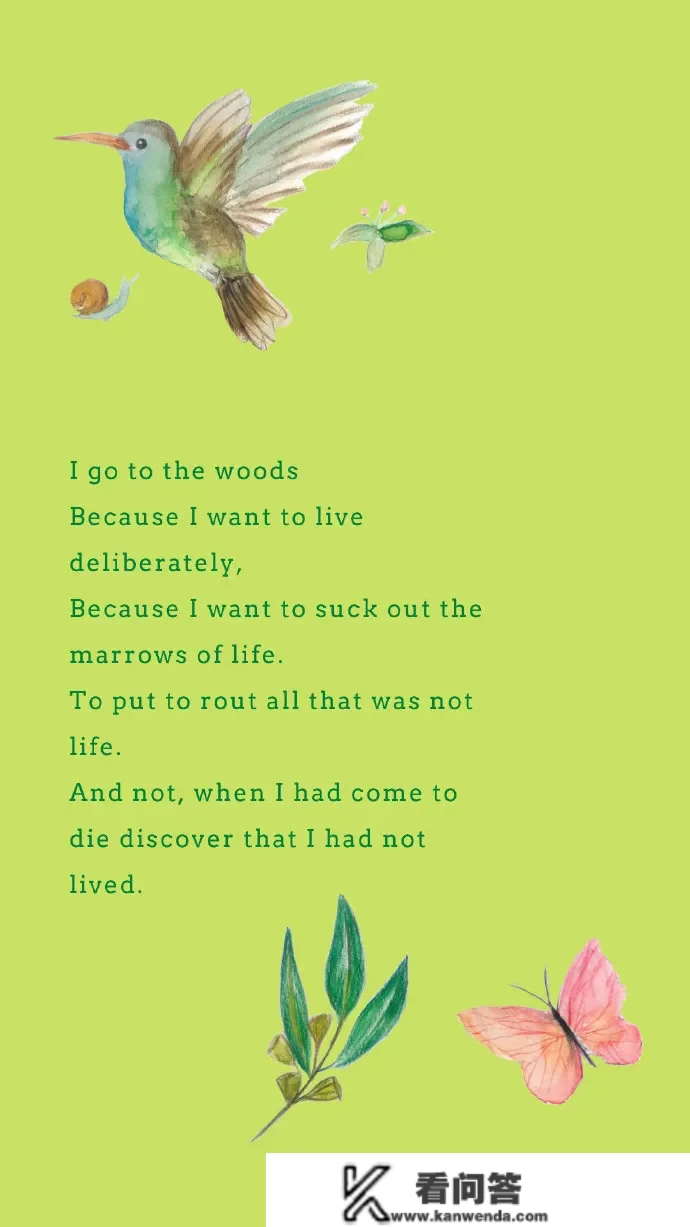 之前画的画,做了书签,配的文字就是那一段。
之前画的画,做了书签,配的文字就是那一段。我想要深切地体验生活,吸收生活全数的精华;
我想要坚决地像斯巴达人[2]那样去生活,
把各类和生活无关的工具通盘击溃;
我要划出宽广的战场,认真覆灭所有的浮华和琐碎,将生活逼到某个角落,剥掉它全数的伪饰,
若是它的实面目是低贱的,那么我就彻底地认清它的低贱,并将其公诸世人,
若是它的素质是高尚的,那么我就实在地去认识它的高尚,并将其照实地记录在我的下一篇游记里。
在我看来,大大都人是很奇异的,他们其实其实不确定生活的素质是什么,到底是属于魔鬼仍是属于天主,
然而却又迫不及待地声称人在那世上的次要目标是“永久为天主增添荣耀和让他感应快乐”[3]。
可是我们仍然生活得很低贱,很像是蚂蚁,虽然神话说我们早就已经酿成人[4];
或者像是与白鹤战斗的俾格米人[5];
那实是错上加错,大错特错,我们因而陷入了一种多余的、本可制止的悲凉境况。
我们的人生被许多无足轻重的工作消耗了。
人实正需要的工具,根本上十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顶多再加上十个脚趾,其他的都是可 以丢弃的。
简单,简单,再简单!

照我说,别去做成百上千件事,只要做两三件就好;
别逃求上百万种工具,只要逃求五六种就好,你的账目只要记在大拇指的指甲上就好。
文明社会就像巨浪滔天的大海,人想要在那片海洋中保存,
想要通过测算汽船的方位和航向顺利抵达港口,而不是沉沦到海底深处,
那么除了波谲云诡的气候,他还得留意其他一千零一种工具;
现实上,他必需是个精于计算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胜利。简单点,再简单点吧。
其他用品也要响应地削减。

我们的生活就像日耳曼联邦[6],由许多小国度构成,疆域线永久变革不定,就连日耳曼人本身也搞不清。
我们那个国度内部拥有许多所谓的先辈设备,不外那些都是外表而浅薄的;
它其实是个难以办理的痴肥机构,充溢着各类脆而不坚的粉饰品,常常落入它本身布下的陷阱,
并且也已经式微破败,因为过于豪侈挥霍,又缺乏计算和高尚的目的,国内数百万户家庭的情况也是如斯;
要挽救那个国度及其人民,仅有的办法是施行厉行节约的经济政策,让人们过上比斯巴达人愈加严酷自律的生活,并进步他们的生活目的。
现在的生活过分匆促。
人们认为那国度有需要兴办贸易,出口冰块[7],借助电线扳谈[8],以及乘坐时速三十英里的交通东西[9],他们对此坚信不疑;
但至于我们应该活得像狒狒,仍是像人类,各人反倒不确定了。
假设我们并没有铺设枕木,锻造铁轨,夜以继日地工做,而是努力于改善我们的生活,那么谁来修建铁路呢?
假设没把铁路修好,我们若何能及时奔赴天堂呢[10]?

但若是我们待在家里,管好本身的事,谁还需要铁路呢?
我们没有骑上铁路,反倒被铁路给骑了。
你有没有想过铁路下方的枕木到底是什么?
其实每根枕木都是一小我,是一个爱尔兰人或者扬基人[11]。
他们身上铺着铁轨,笼盖着黄沙,任由火车霹雷隆地驶过。
我告诉你吧,他们是长逝不起了。
每隔几年,会有新的地盘被铲安然平静铺设上轨道;
既然有人得到了乘坐火车的快乐,那么必定有人接受了修建铁路的痛苦。
摆错处所的枕木就像梦游的人,
人们如果发现如许的枕木,就会突然刹停火车,对着它少见多怪,似乎那是稀有的破例。

据说每五英里就有一个铁路道班,他们的责任是让枕木原封不动地躺着,
我听了感应很快乐,因为那意味着它们有时候仍是会站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过着如斯匆促和浪费的生活呢?
我们明明肚子还饱着,却担忧会饿死。
人们说及时缝一针,未来省九针;
所以他们为了在明天省九针,不吝在今天缝上一千针。
至于工做,我们的工做都是毫不重要的。
我们得了跳舞病[12],无法让我们的脑袋连结静行。
若是我敲响教堂的钟,发出走火的警报,那么在康科德镇周边农场干活的人必定是会赶过来的,哪怕他今天早上说过几次他有良多工作要做;
我敢说无论男女老幼,城市抛下手头的活计,跟随钟声而来,次要倒不是想来救火,
诚恳说吧,各人都有点幸灾乐祸,更多的是想看那火烧得有多旺,因为那火又不是我们放的;
或者来看看那场火是若何被扑灭的,若是火势不大,也许还会插手帮手;
是的,哪怕着火的是教堂自己,人们也会是如许的[13]。
有人吃了午饭打盹才半个小时,醒来时却昂首问:“有什么新闻吗?”
似乎其别人全都在替他刺探动静。
有些人睡觉时叮咛他人每隔半小时就把他叫醒,无疑也是出于不异的目标;
然后他们会礼尚往来地说出他们梦到了什么。
颠末一晚的睡眠,新闻变得像早餐般必不成少。
“请告诉我那地球上有什么新闻,随意发作在哪小我身上的都能够。”

于是他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卷,翻阅起报纸,看到今天早晨有人在瓦奇托河畔被挖掉了眼珠 [14],
浑然不觉他其实生活在那世上某个深不成测的暗中巨洞[15]里,而他本身的眼睛尚未发育完全[16]。
对我来说,邮局是无关紧要的工具。[17]
我认为它传递的重要信息十分少。
说句欠好听的,我那辈子收到的信,值得花那邮费的不外一两封————那句话是我在几年前写的。
凡是来说,便士邮资[18]那种轨制,原来是让你庄重地用一便士来交换对方的思惟,可是你得到的往 往是废话。
我敢说我历来没有在报纸上读到什么严重的新闻。
我们读到的无非是有人遭掳掠了、被谋杀了、不测身亡了,或者有房子失火了,或者有货轮沉没了,或者有蒸轮船爆炸了,或者有头牛在西部铁路[19]上被碰死了,或者有条疯狗被杀死了,或者冬天呈现了许多蝗虫——如许的报纸我们不需要看第二份。
看一份就够了。

若是已经掌握了某个原理,你怎么还会在乎它那千变万化的例证和应用呢?
可惜热衷于阅读那些蜚短流长的人还不在少数。
传闻前些天有良多报酬了尽早读到最新的外国新闻,把某个邮局的玻璃挤破了好几块——至于那条新闻,
我实心觉得一个伶俐人在十二个月或者十二年之前就能足够详细地写出来。
就拿西班牙来说吧,该国的工作无非就是唐卡洛斯和那位公主的争权夺[20],唐佩德罗在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之间的比年征战[21],顶多再加上斗牛和其他娱乐活动;
只要你能把那些工作写清晰,就等于把西班牙的现状原本来当地告诉我们,并且其准确水平,将丝毫不亚于报章上那些简明扼要的西班牙新闻。
至于英国,阿谁处所比来一条重要的新闻是1649年的革命[22];
并且当你领会该国粮食的年均产量之后,你就不消再存眷那类动静了,除非你想通过倒卖粮食来赚点钱。
人用不着经常看报纸,也能够判断外国少有新的工作发作,其实就连法国大革命[23]也不算是新闻。
狗屁新闻! 更重要的是去领会那些永不外时的工具!
卫国的大官遽伯玉派人到孔子家去刺探动静。
孔子请那人坐在本身身边,并如许问他:“你家仆人比来忙些什么呢?”
那信使恭敬地答复说:“我的仆人想要削减他犯的错,可是怎么减也减不完。”
使者走后,那位愚人感慨说:“实是个好信使啊! 实是个好信使啊!”[24]我认为歇息日,应该算是每个礼拜的最初一天[25],
因为礼拜天很合适对虚度的一周停止总结,而不是让人精神振作地去驱逐新的一周的日子。
在那一天,牧师与其用三言两语的传教,去骚扰那些昏昏欲睡的农夫的耳朵,
倒不如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呐喊:“且慢!且慢!你们为什么貌似走得很快,其实却慢得要死?”
现在谎话与幻觉被捧为至高的实理,现实反倒变得荒唐。
其实人们只要始末认清现实,不让本身受棍骗,那么生活将会变得像童话般美妙,就像《一千零一夜》[26]那样。
若是我们只推崇天然的、高尚的事物,音乐和诗歌将会响彻街头巷尾。
在沉着而明智的时候,我们发现唯有伟大而崇高的工具,才是永久而绝对的存在——至于那些琐碎的忧惧与 *** ,那不外是现实的影子。
那种形态是欢乐而纯洁的。
可惜人们往往是自觉而懒惰的,甘愿受各类幻象棍骗,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许多端方和习惯,而那些端方和习惯的根底,也仍然地道是虚幻的。

儿童把生活当做游戏,反而能更清晰地认识生活的实在规则和各类关系;
大人没能过上有价值的生活,却自认为愈加伶俐,因为他们有经历,可惜他们的经历其实就是失败。
我曾在某本印度的书上看到:“畴前有个王子,自幼被流放出境,由樵夫抚育;
在如许的情况里长大成人后,他认为本身属于低贱的社会阶层。
后来他父亲有个大臣发现了他,向他透露了他的出身,于是他对本身身份的错误认识便消逝了,末于大白本身是个王子。”
那位印度哲学家接着说:“其实灵魂也是如斯,它老是错误地认为它属于所处的情况,曲到某位上师向它揭露了本相,它才大白本身就是婆罗贺摩。”[27]

我觉得我们新英格兰地域的人会过着如斯猥贱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穿事物的表象。我们认为表象就是素质。
若是有人走进那座城镇,只看到现实,你觉得他看到的镇中心是什么样的呢?
若是他把在那里看到的现实境况描述给我们听,我们应该辨认不出他所描述的处所。
大礼堂也好, *** 大楼也好,或者是监狱、商铺和通俗室第也好,
只要你实正用心地去看,你看到的素质将和你以往看到的表象完全差别。
人类爱崇的实在都很遥远,在太阳系的外围,在最遥远的星辰后面,在亚当之 前,在人类末日之后。
永久的范畴确实有些实在而高尚的工具。
但所有的时间、地点和境况都是此时此地。
天主自己在此刻即是最神圣的,绝不会跟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加神圣。
只要持续不竭地渗入和浸泡在四周的现实之中,我们才气理解一切纯洁而崇高的工具。
宇宙老是驯服地回应我们的设法;
不管我们走得快仍是慢,路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所以让我们思维清晰地生活吧。
纵使是那位诗人或者说艺术家,也从未拥有如斯美好而崇高的做品,但至少他的后代可以完成它。
让我们如大天然般悠然自由地生活一天吧,别因为有坚果外壳或者蚊子同党落在铁轨上而翻了车[28]。
让我们该起床时就赶紧起床,该歇息时就放心歇息,连结平和平静而没有干扰的心态;
身边的人要来就让他来,要去就让他去,让钟声回荡,让孩子哭喊————下定决心好好地过一天。
我们为什么要轻言放弃和趁波逐浪呢?
让我们别为一日三餐懊恼,别被如斯可怕湍急的漩涡淹没。
只要涉过那段险滩,你就会平安无事,因为剩下的都是容易走的下山路。
抖擞起来,带着早晨的活力,启航前进吧,寻找其他的航线,像尤利西斯那样,把本身绑在桅杆上[29]。
若是火车头突突地吼叫,就让它吼到嘶哑吧。
若是钟声响起,我们为什么要渐渐赶路呢?
我们倒不如认真听听它像是哪种音乐。
让我们把本身安放下来,好好地工做,用力去踩踏脚下的烂泥,
那由成见、成见、传统、谎话和表象搅成的烂泥,去踩那遍及全球的脏水,那污染了伦敦和巴黎、纽约和波士顿和康科德、教会和国度、诗歌和哲学和宗教的脏水,
曲到我们的脚触及坚硬的底部和平稳的岩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然后我们说:“没错,就是那里。”
有了那个安身点,你也答应以在洪水、迷雾和烈焰之下,成立一面墙壁或者一个国度,或者平安地竖起一根灯柱,
又或者能够安个丈量仪,不是丈量尼罗河水位那种,而是丈量现实的,以便未来的世代可以晓得,谎话和表象的洪水曾经储蓄积累得有多深。
若是你勇于面临各类事实,你将发现太阳的两面城市发光,似乎它是一把双刃剑,
并且你将感触感染到它那美好的锋刃正在剖开你的心和髓,到时你会快乐地完毕你在俗世的事业。
不管生仍是死,我们只渴求现实。
若是我们实的就要灭亡,让我们聆听本身喉咙里的咔嗒声,感触感染本身四肢的冰冷吧;
若是我们还活着,让我们为本身的工作奔波吧。
时间无非是供我打鱼的河流。
我在河边喝水,但在喝水时,我能看见全是沙子的河底,于是大白它有多浅。
时间的浅水潺潺流过,但永久仍然存在。
我愿意到更深处去喝水;

我愿意到天空里打鱼,天空的底部铺满了星星。
我不懂数数。
我不认识字母表的之一个字母。
我老是懊恼本身不如刚出生时伶俐。
智识是一把砍刀;
它会探测和切开事物的奥秘。
我不希望我的双手去忙多余的工作。
我的思维是双手和双脚。
我觉得我更好的本事都集中在它里面。
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思维是挖洞的器官,有了它我能够在那些山岳里开采和发掘。
我想最丰硕的矿藏就在那附近某个处所;
那是我按照探测棒和升腾的薄雾判断出来的;
我要在那里脱手开采。
参考^清醒地生活是梭罗更大的人生哲学,从那个意义上来说, 他堪称目前在西方十分流行的新时代哲学的前驱。 ^斯巴达是古代希腊城邦,其人民以严守规律、生活朴实著 称。^那是其时的教义问答上常用的句子。^在希腊神话中,厄诺庇亚国王埃阿科斯在其国民因瘟疫而 灭绝之后,哀告他的父亲宙斯从头赐给他一些子民,于是宙斯将一株 老橡树里所有的蚂蚁都酿成了人。^荷马在《伊利亚特》第3卷开篇将特洛伊人比方成与俾格米 人战斗的白鹤。俾格米人是希腊神话中的矮人族,后来泛指所有全族 成年须眉均匀身高矮于150厘米或155厘米的种族。^日耳曼联邦:指欧洲中部39个独立的日耳曼国度构成的松 散联邦,成立于1815年,闭幕于1871年,那年奥拓·冯·俾斯麦 (Otto von Bi *** arck,1815-1898)同一德国,创建了德意志帝 国。^将新英格兰的冰块出口到炎热的印度等地是昔时新兴的产 业,更多详细情况可拜见本书第16章“冬天的湖泊”及相存眷释。^指其时刚呈现的电报。^1844年通到康科德镇的火车是人类汗青上之一种到达那个 速度的交通东西。^梭罗的伴侣纳撒尼尔·霍桑曾写过短篇小说“天堂铁 路”(The Celestial Railroad),收录在1846年出书的短篇小说集 《旧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中,请拜见该书第 173-192页。^枕木的英文是sleeper,也有睡眠者的意思,所以下文梭罗 说“他们是长逝不起了”。昔时铺设铁路的工人大大都是爱尔兰移民, 或者美国东北部地域穷苦的当地人。扬基人是美国东北地域、尤其是 新英格兰地域人民的统称^跳舞病:又称风湿性跳舞病。常发作于链球菌传染后,为 急性风湿热中的神经系统症状,临床特征次要为不自主的跳舞样动 做,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尤以5-15岁女性多见。^1844年4月30日,梭罗和他的伴侣爱德华·霍尔(Edward Hoar,1823-1892)无意间引起了一场丛林火灾,销毁了300英亩 林木,形成超越2000美圆的丧失。梭罗不断为那件工作感应十分愧疚。^瓦奇托河是美国南部的河流,流经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 州。据说本地的印第安土著打架时会用大拇指去挖掉敌手的眼珠。^梭罗在那里想到的是美国肯塔基州的猛犸洞(Mammoth Cave),如今世界上已知的溶洞系统中更大的一个,截至2006年已 探明洞窟总长度达350英里。^猛犸洞里生活着一种盲鱼,因为常年不见天日,那些鱼的 眼珠始末没有发育完全。^现实情况并不是如斯,梭罗生前写了良多信,美国粹者罗伯 特·哈德斯佩思(Robert Hudspeth)目前正在为普林斯顿大学出书 社编撰多达三卷的《梭罗手札集》。^1840年1月10日,英国邮政总局设立了便士邮资轨制,规 定了全国同一的邮费,重量在一盎司以下的信件邮资只需一便士,并 发行了邮政史上出名的“黑便士”邮票。在1850年,美国平信的邮资 是三美分。^指马萨诸塞州西部铁路,1841年开通,毗连波士顿和纽约 州的奥尔巴尼。^1808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1748- 1819)被迫下台,让位给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 1784-1833)。1830年5月,斐迪南七世颁布法令,规定女性也可 以成为皇位继承人;同年10月,斐迪南七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诞 生,代替了她的叔父唐·卡洛斯亲王(Infante Carlos,1788- 1855),成为西班牙国王的之一继承人。1833年,斐迪南七世去 世,心怀不满的唐·卡洛斯颁布发表本身成为西班牙国王,并与撑持伊莎贝 拉的戎行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内战。1843年,年仅13岁的伊莎贝拉顺 利加冕,成为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 II,1830-1904)。^唐·佩德罗即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佩德罗一世(Pedro I, 1334-1369),从1356年起,佩德罗一世不竭地与阿拉贡王国的佩 德罗四世(Pedro IV,1319-1387)停止战争,但百战百胜,先后 从托莱多、塞维利亚撤离;在1369年,佩德罗一世在安达卢西亚大 区的格拉纳达阵亡。^1649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将英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 成立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短暂地拔除了该国君主造。^指1789-1799年发作的法国革命。^《论语·宪问第十四》:“遽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 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 曰:‘使乎使乎!’”梭罗是从让-皮埃尔·纪尧姆·鲍狄埃的《孔子与孟 子:中国道德和政治哲学四书》第184页上看到那个故事的。^在西方,人们遍及把礼拜天视为每个礼拜的之一天。^《一千零一夜》:一部 *** 民间故事集。^引文出自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等人翻译的古印度典范 《数论颂》,拜见该书1837年版第72页。婆罗贺摩便是梵天,在印 度教中,他是缔造之神,与毗湿奴、湿婆并称三主神。^早期的火车很容易因为铁轨上有杂物而脱轨。^在荷马的《奥德赛》里,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曾将自 己绑在桅杆上,以便抵御海妖魅惑的歌声。